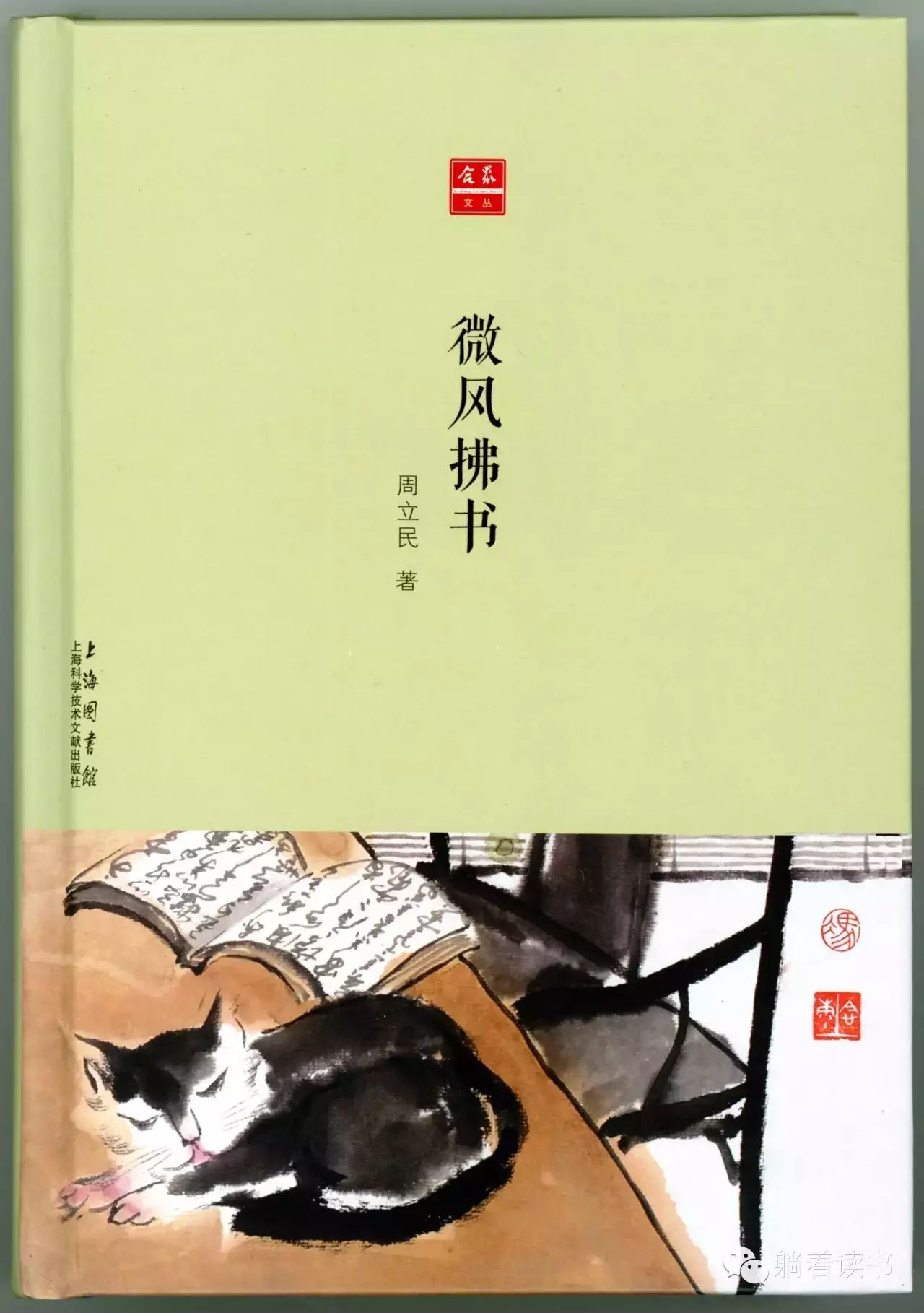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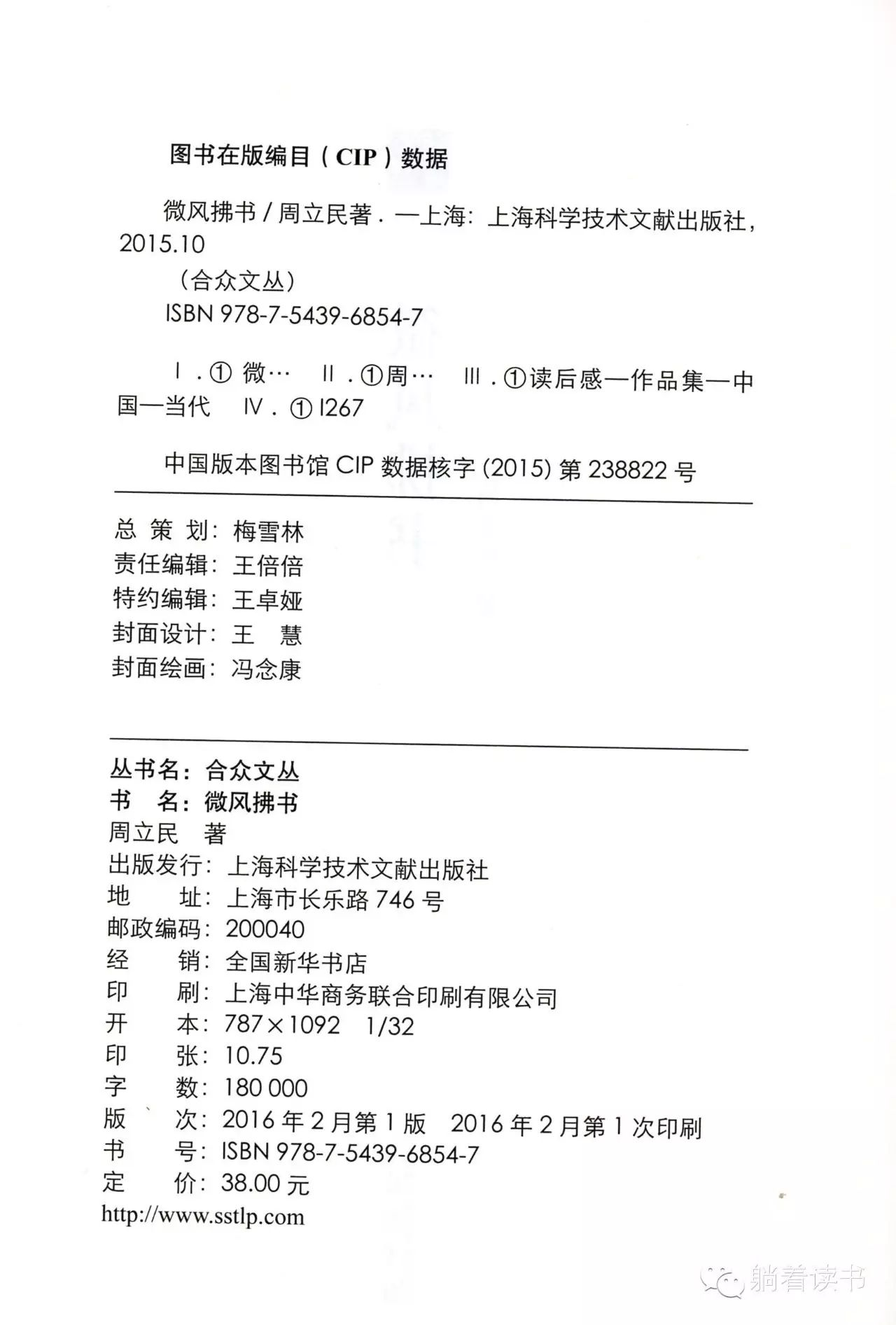
《随风飘荡的书》后记
有一次我坐在刚成立的网络作协负责人臧先生旁边,半开玩笑地问他:嗯,我每天都在微博、微信上写作,一个月就有不少“创作”,我能加入网络作协吗?臧先生很认真地回答我:还不行,你得把作品发表出来。就这样吧。我说的是实话,每天坐地铁或者下班回家,都会发一条只有一二百字的微博,没想到时间长了,下载下来,一个月就有近万字。我一开始还挺震惊的。微博、微信除了打发时间、有信息灵感的时候写作,似乎还承担了一些读书笔记的功能,就像古人的笔记一样,边走边记,把思考写下来。 不像古人,几百年后才有机会与他人交流,而现代科技让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即时回应他们的反应。这是一种难得的分享书籍的体验,当然,是零散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或者说,边读边想。但把它们拼凑起来也是好的,这样我就能看见自己在一段时间里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虽然不像写文章,但我也是认真的。本书“万花筒”系列收集的文字,都是微博的精选。当然,这和你是否是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无关。新媒体虽然是无法阻挡的洪流,但我想,它只是为了方便信息交流,或者让我多了一个阅读的手段。我既不慌不忙,担心没人看纸质书,也不把它当成洪流,拒绝雅俗。我是食人族,黑白分明,随心所欲。 比如我出门旅行,不仅会带上几本纸质书,还会把很多电子书拷贝到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里,边看边读。对于阅读,无论怎么变,都是不变的。说白了,它永远需要我们一字一句地去读,去琢磨,去回味。
这依然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是我上一本读书笔记《读书时光》(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的延续。按照我的惯例,我依然不收录论文性质的文字,只收录读书随笔。我更喜欢这种灵活的表达方式。读书不只是读书,也是读人、读世界;读书也是通过书读“我”。随笔有一种开放性和灵活性,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不像论文那样死板,好像被挤干了,就变成硬邦邦、干瘪瘪的栗子,嚼不动。而且读书就像把玩一个五彩缤纷的瓶子,没有任何功能。首先,我被那些色彩吸引。更重要的是,这些色彩并不单调,赏心悦目。这是一种氛围,一种意境,但不是心灵鸡汤,不是养生秘诀,也不是成功秘诀。我们身在其中,却觉得有趣、快乐。它们对我们的滋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这是一种自然的熏陶和无意识的渗透。我喜欢读书,但不喜欢把它变成“必然”、“必要”或“必须”的事情。读书本身也需要摆脱束缚,获得自由。
为此,我打开自己的“五斗橱”,找出几篇近二十年前写的旧作,虽然已蒙尘,稚嫩,却不忍丢弃。那时还是另一个城市,我满腔热情,感到孤独,排解孤独的唯一方法就是读书。最怀念的,是那时悠闲地读书。读完书,没有编辑等着我写书评,于是,我便写得很多,只是写自己所感所想,忍不住要写。那些是我所珍惜的往日时光。在不那么紧张的节奏中,书页之间,我与阳光灿烂的日子告别。这本集子的最后一篇是《枕浪夜读录》,这不是梦话,而是现实的描述。那座城市,在两海的怀抱中,我的住处离海那么近,步行过去,只需要十几二十分钟。夜深人静,大海还在哼唱,歌唱。 随着它的节拍,我游走在虚幻的海洋中,现在想想,似乎很有诗意,但当你身在其中,却不会意识到时间已经如手中的水一样流逝,慢慢地流走了。
有一年春天,我在整理这篇稿子,断断续续,一遍又一遍地拖出来,仿佛有一段记忆不忍打破。怀念那些自由阅读的日子,怀念那些陪我走过时光森林的人。岁月流逝,时光不再,很多人和事都过去了,但无论时间多么残忍,也无法带走我的记忆,它们或许还像云雾一样飘浮在我的脑海里。有些也化作文字,成为这样一本小书。所以,我将这份心意献给和我有着同样记忆的朋友!
周利民
2015年5月2日凌晨,上海竹小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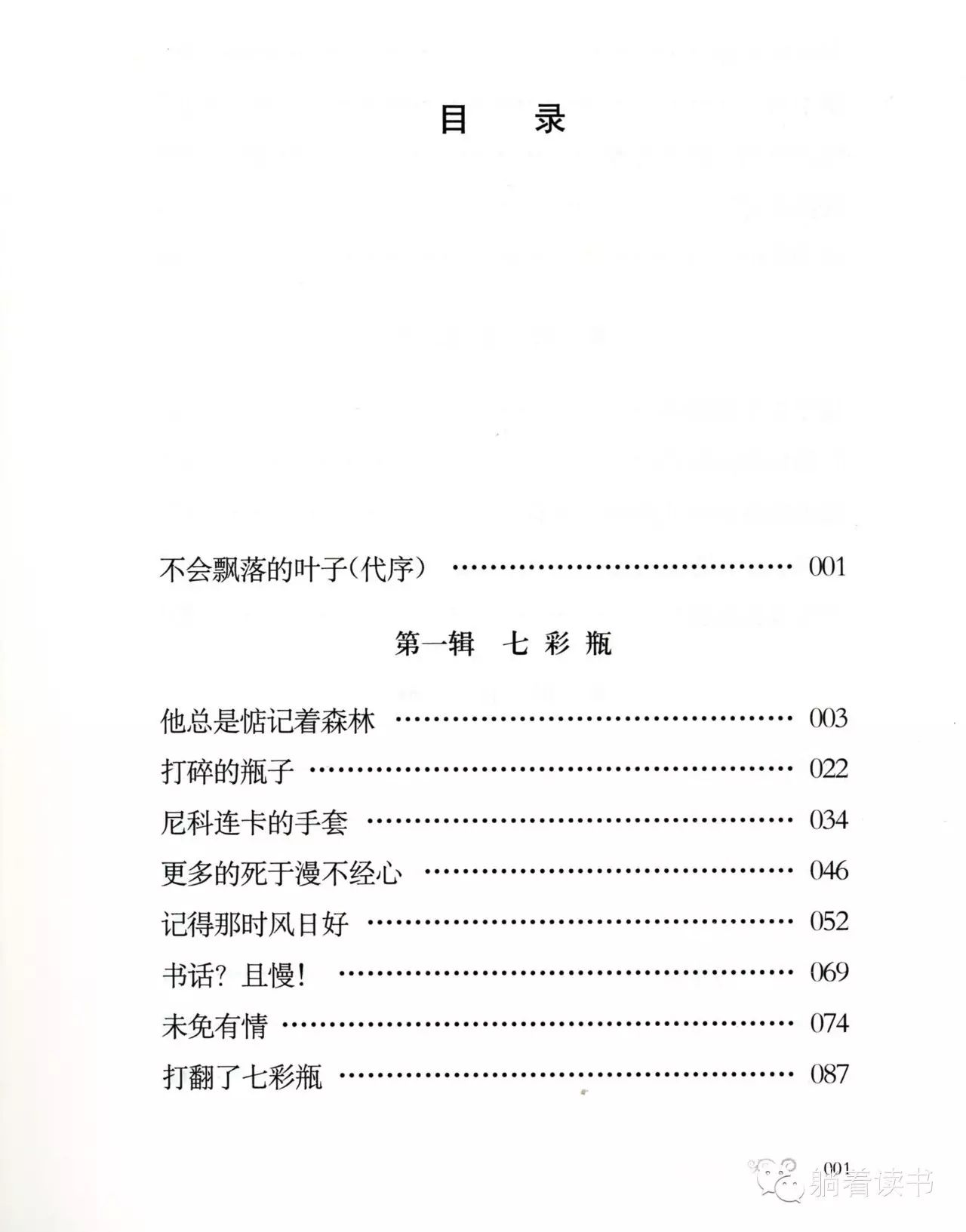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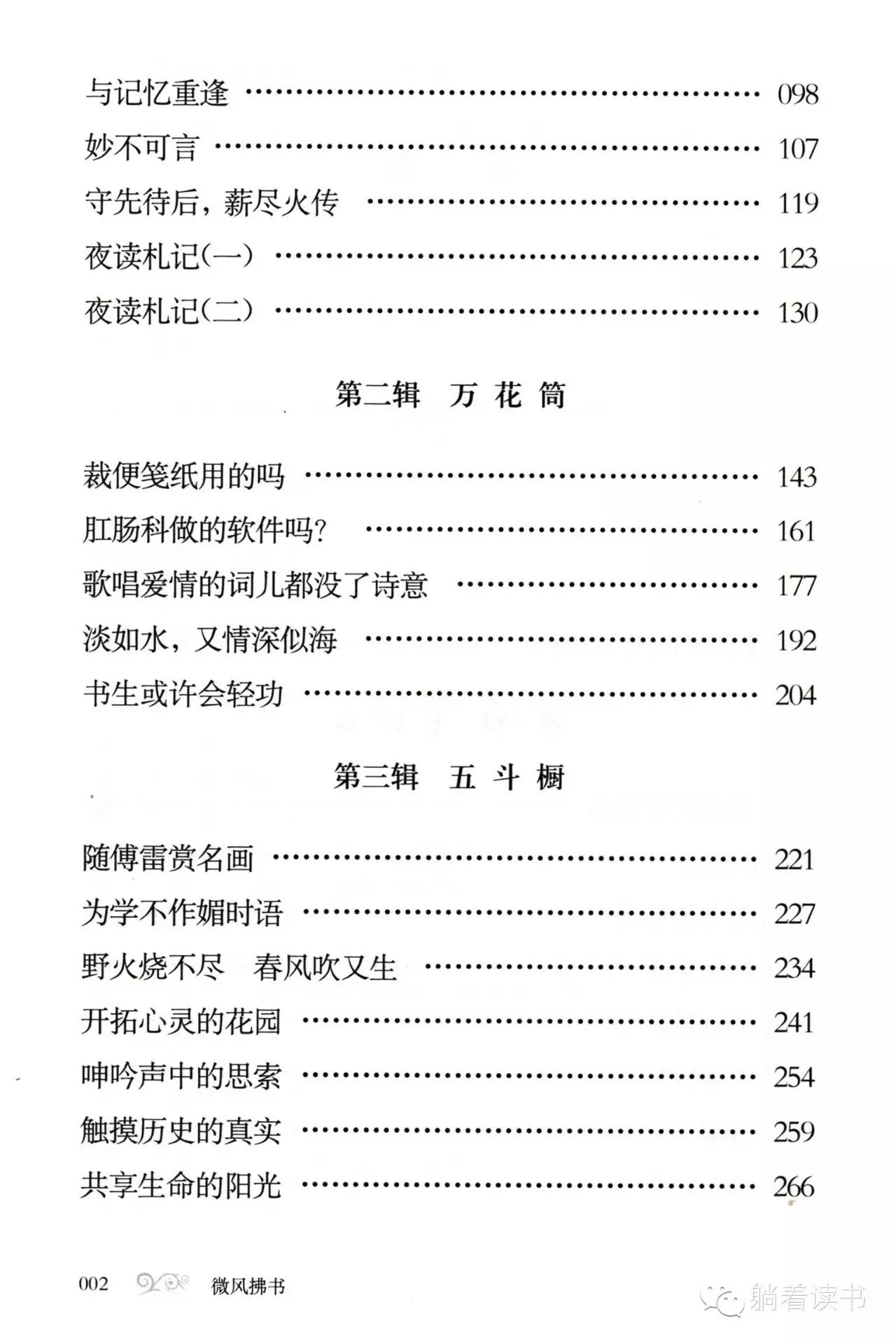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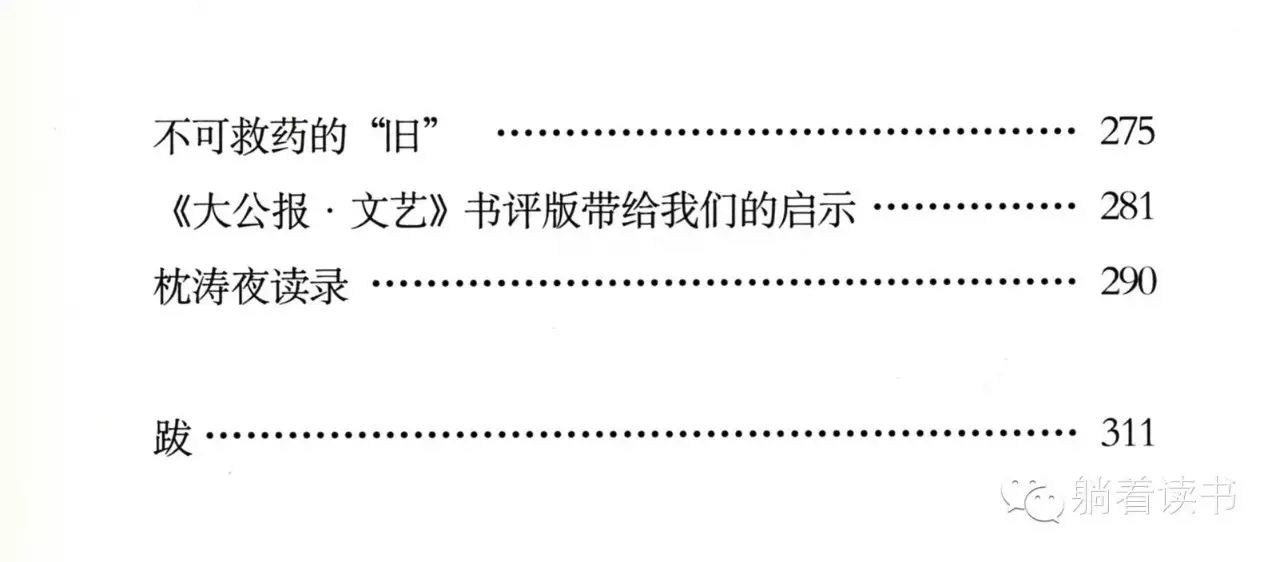
轻如水,深如海
阿来在《草木理想国:成都物候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一书中谈到前年春天的一次活动,在成都附近的三岔岛,“还在开会,和同事们开会,聊天喝酒喝茶……连续下了两天的雨,岛上和环岛的湖面都笼罩在雾气中,像烟雾一样。”那次我也在场。在孤岛上,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大家聊得更开心了。一天晚上,喝着飘雪,我也听了阿来的谈话。当然,有些人已经喝醉了,说不出话来。(5月2日,17:31)
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以《花园711号》为题发表于《作家》杂志2012年第1期,附有大量照片。由于文章中有很多植物、昆虫、动物,照片自然清晰,锦上添花。但书出版时,只剩下文字。阿来的《花草树木的乌托邦》也是一套书,有照片,而且是彩色的。为什么偏爱其中一种呢?一本书如果不能以最合适的形式制作出来,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老话:梨灾枣灾。(5月3日21:56)
我拿到了王安忆的《时间里的空间流动》(新兴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粗略地翻了翻。很多文章我都看过。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在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明确标注了写作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应该遵守的写作道德。现在的作家经常在同一篇文章上编辑,却把时间抹掉,让读者搞不清楚时间和空间,这是不对的。更糟糕的是,有人甚至连标题都改了。(5月3日 23:37)
杨志水1992年2月15日日记:“我又去见顾林先生……拿回《清诗纪事笔记》给他审阅。顾林先生说:劝人时,忌冷嘲热讽,故我在语气上多加修改。”——可见老一辈的人品和文德,谈学问都是出于善意,不像今天那些自视甚高的人,自视甚高,用显微镜把别人的浅薄知识放大,只为显示自己的智慧,其实只露出自己的小气。(5月5日08:49)
终于有空了,上午赖床,把《十年读书》[下](杨志水著,中华书局2012年1月出版)读完了。发现有些错别字,比如复旦大学教授“蒋文华”,应该是蒋逸华吧?上海的“西平路”明明是四平路。多半是输入错误。巴金全集的两卷日记也有类似的错误,用的时候才发现。(5月6日18:51)
杨志水1992年3月22日来信说,她到新雅公寓看望陈思和。“进门就很吃惊,地板是木板铺的,四周也是木壁板,门窗和屋内一切家具都与之相配,颜色、款式都很协调,很雅致,很干净,很有老式建筑的味道……原来是主人花了几万元自己设计,又雇人装修的。”以前我去的文人家,都是没有装修的,所以才这么吃惊。(5月6日18:34)
杨志水提到的陈思和先生的家,就是他的黑水斋。书架设计很特别,每个隔间都加了一个阶梯式的底座,前后两排摆放着书籍,翻过第一排书架,便能看见前排书的书名。我刚来的时候很惊讶,为什么会有丰子恺的画?仔细一看印章,才知道是丰逸隐。这两年,陈先生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个名字:余教乐斋。虽然有题词解释,但我还是看不懂。(5月6日 18:44)
成为最真实的自己,可以成为人生的目标。很多时候,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有时知道却还要装作别人。前者让人活得很痛苦,后者让人活得很累。遇到一些公众人物,他们的话语从不提及自己的大脑和感受,却总是想着如何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样活着,既累又难过。(5月5日 06:12)
@上官秋晴:“所有的学习,所有的观察,所有的体验,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欲望……对我来说,唯一的目的就是了解自己,成为最真实的自己,最终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我逐渐领悟到的方法,也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通过靠近自己喜欢的一切来实现。她一直鼓励我做自己喜欢的事,禁忌就是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
因为要查典故,我把家里的书都拿出来,《英美文学与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希腊罗马神话》、《古希腊传说与神话》等,却发现无一例外都没有名字的索引。我又不是过目不忘的天才,只好翻着找。出版社以为索引是浪费纸张,却不知道这会大大方便读者。这时,我觉得电子书会取代纸质书,它的搜索功能太方便了!(5月8日 17:21)
补充:《康德传》(曼弗雷德·库恩,吴天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全书651页,其中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占了475至650页,接近180页,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以上。总有人舍不得丢掉这些纸吧?不管这些内容有多大价值,哪怕是全书的一部分,也不应该随意丢弃。一个严肃的作者,一定有他不辞辛劳列出这些信息的理由。
清少纳言说:“梨花很令人失望……就花色而言,没有什么趣味。但到了唐代,文人视其为奇观,写下不少有关梨花的诗篇,想必其中必有原因。”日本人为何如此不喜欢梨花呢?在我的家乡,梨花是村落的华丽衣裳,梨花盛开也是春天结束、夏天来临的信号。尤其是老树开出新花时,花显生机,树显沧桑,还是很吸引人的。(5月8日 17:40)
董桥在近作《如月》中,写到一位叫伊丽莎白的女士,晚年爱读中国诗歌。她八十多岁去世前,曾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说她已经把韦利翻译的《一百七十首中国诗歌》读了第十遍……这正是我羡慕的读书方式,挑喜欢的书一遍遍地读,百读不厌,每读都有收获。可惜喜欢的书太多,嚼不烂。希望退休后,能提着一筐书回到故乡,细细地读!(5月9日 20:35)
沈从文在《私塾里》一书中,激动而混乱地谈起了逃学的乐趣,并说:“我实在找不到一点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所需要的日常死记硬背的学习。我想玩,但似乎比吃饭睡觉更重要。”野孩子都有逃学的经历,但现在乖巧的小男孩根本不知道逃学是什么感觉。曾经有朋友说,他的儿子因为某事缺课而焦虑。对此,我大声疾呼:如果一个男孩到了大学还不逃课,那他不是完了吗?(5月10日 08:54)
刚从季风拿回来张儒伦的《存在与时间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厚厚的两册,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床头柜上堆了那么多新书!看书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买书的速度,虽然我反复把节奏控制在两者之间,但还是读得很慢,我很焦虑。总有人说读书日、读书节之类的,怎么就不提读书假期呢?假期在家看书,很节能环保,对吧?(5月11日 22:32)
我正在读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书中描述了台湾多年的政治恐怖,以及它给无数家庭带来的苦难,以及苦难中闪光的人性。这本书应该和《大河》一起读,因为它写的是齐邦元没有写或没有写到的东西。把两本书放在一起,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台湾。同样的历史,完全不同的记忆。但孙的书可能不符合一些人的阅读期望。(5月12日 10:47)
我同意志安教授的做法,如果研究者要研究版本,可以去图书馆查,这是必备技能。版本中的贞洁情结对收藏者和研究者更有用,对读者来说未必。最重要的是,这是作者的书。重印一本书,尊重作者的意愿是起码的。(5月13日 10:47)
@止庵:我觉得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修改、补充的权利应该被承认和尊重,所以我不会用第一个版本。
@止庵:《周作人译本全集》有三个特点:一是选集,二是译文,三是注释。周作人译作多为世界文学经典;他从不主张用明显不符合原文“气氛”的汉语美或丑来代替原文之美;注释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占其译作的很大比重。晚年的周作人游离于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保证了注释不受时代限制,价值历久弥新。
上周去枫泾丁聪漫画馆,花了十块钱买了一本《小丁与三联书店》,这是三联书店2009年6月出版的“内部读物”,没有书号,内容很简单,就是小丁和“读书”、漫画、朋友等内容。很喜欢这样温馨有纪念意义的书刊,如果不去书店,少了很多商业气息。他们还给范勇做了一本书,不知道三联还给谁做过这样的非员工刊物?(5月13日 17:07)
我从人文出版社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本新版的《灾后十种作品》。这本书能再版,我非常高兴。千禧之际,我买的是山东画报版,是绿色封面的小版。那时,我还在大连。在那个颇为寂寞的城市里,孙犁朴实、隽永、平易近人的文字陪伴我度过了漫漫长夜。如今,它已改成了32页的长条,也颇具特色。这本书的再版,让我有机会再次读到这些令人难忘的文字。(5月14日 13:39)
诗人于坚在《昆明笔记》中写道:“在步行一小时没有水果店的旱街上,看见一群城管抢走了卖杨梅的山姑娘的担子。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爬山摘那些长满毛的杨梅。城管有不可置疑的理由,他们破坏了市容市貌。山姑娘站在街上,拿着空秤哭泣。”多年前我读过这段话,至今忘不了“长满毛的杨梅”和姑娘的眼泪。(5月21日 12:25)
昨晚读了野夫的《何处是我故乡》(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版),又一部血泪家族史。《流放书房》一文中写道:“书生生活艰难,漂泊无定,自古如此。但我知道,尘埃里,包袱里,只要(而且必须)带几卷诗书,那么,无论路途多远,多孤独,都不会太过凄凉。”这是书生在悲凉中的自我安慰。(5月21日 12:13)
晚上读孙犁的《晚花》,谈及朋友:“我所敬重的同志们,都是淳朴老实的人,他们的心胸对我而言,就像敞开的大门和一潭清澈的水……我讲了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也提到了他们的缺点。我觉得,不管生死,朋友和同志,都应该如此。”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深如海。不是那么世俗,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看来,只喝酒吃饭的朋友多了,同党、志趣相投的朋友多了。(5月20日 00:27)
二十年前,孙犁先生说:“我桌上放着几本近几年出版的精装书,大多装订不当,材料还行,但做工实在差,大多难以检查,阅读时不能平放。操作人员大多是农村妇女,不是专业人员。”但他们不知道,城市妇女也是这个水平,她们天天嚷嚷着要造出版航母,却连一颗螺丝都不会造。难道她们不知道,做文化需要耐心,每一针一线都要缝。如果孙犁还活着,他会惊呼:农村妇女的孩子又来了!(5月27日 09:09)
90年代,陈思和和几个学生编了一套《走向世纪末的小说选》。那时候王小波还没被崇拜,红克也没写出那么多东西,很多名字不为人所知,但作品让人过目不忘的作家,都入选了。可惜,五卷之后就夭折了。昨晚居然梦见新一卷出版了,还能清清楚楚地读到书里第一本入选的小说,可惜醒来后,我记不清是哪本了!(5月25日 08:32)
@必有妮名不可吗:好像要出新世纪十年来的小说精选了。
回复@必有妮名不可吗:听说过,希望它有当年那样的眼光和才华,如今选集的选编者的随意和粗心尤其让人失望。
@书男张利:当时我还在读大学,至今还记得看完这套书后的震撼,像杨正光的《老丹是一棵树》等等,看完后回味无穷。
@陈村:这本书很好。@朱伟也曾想每年评选一本书,可惜没有实现。
如今世间好坏参半,不是不需要选集,而是需要精心挑选的选集。坦白说,很多选集几乎就像编辑的好友列表。虽然没人说,但大家真的蠢到连最基本的好坏都分不清吗?我不信。(5月25日 15:15)
新版《赵树理全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号称是插图本,收录了不同时期的小说插图,实属罕见。只是开本和印刷太差,但也为集子出版提供了范本。能不能出插图本?尤其是有些插图堪称经典,毕竟书不是一次性消费品。说真的,如果要传给后代,花点功夫也是理所当然的,至少让你的孙子孙女有值得骄傲的东西。(5月22日 20:31)
郑振铎1929年为《爱的故事》所写的序言中,曾自豪地提到这些插图:“其中有些是我在伦敦、利物浦、巴黎、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收藏的。特别是拉斐尔画的天花板壁画,我们好像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图画,如今已不复收录在《郑振铎全集》(华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中。这种通过重印让书籍消失的能力,是当代出版界的不朽成就。许多20世纪50、60年代的名著,在70年代末重印时,还留有各种铜版画等插图,但在80年代末重印时,却一去不复返了。(5月21日18:51)
朋友送了一本《最大的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乔麦的小说出版已经一年多了,我却浑然不知。在《收获》副刊上读到它,仿佛跟着作者的笔回到了过去。十年前的一些事,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如果不是因为写下了回忆,有些事可能已经遗失了。书里有青春的倔强,有沧桑的皱纹,有淡淡的抒情。不错的小说。(5月29日 15:37)
(选自周利民著《微风吹来的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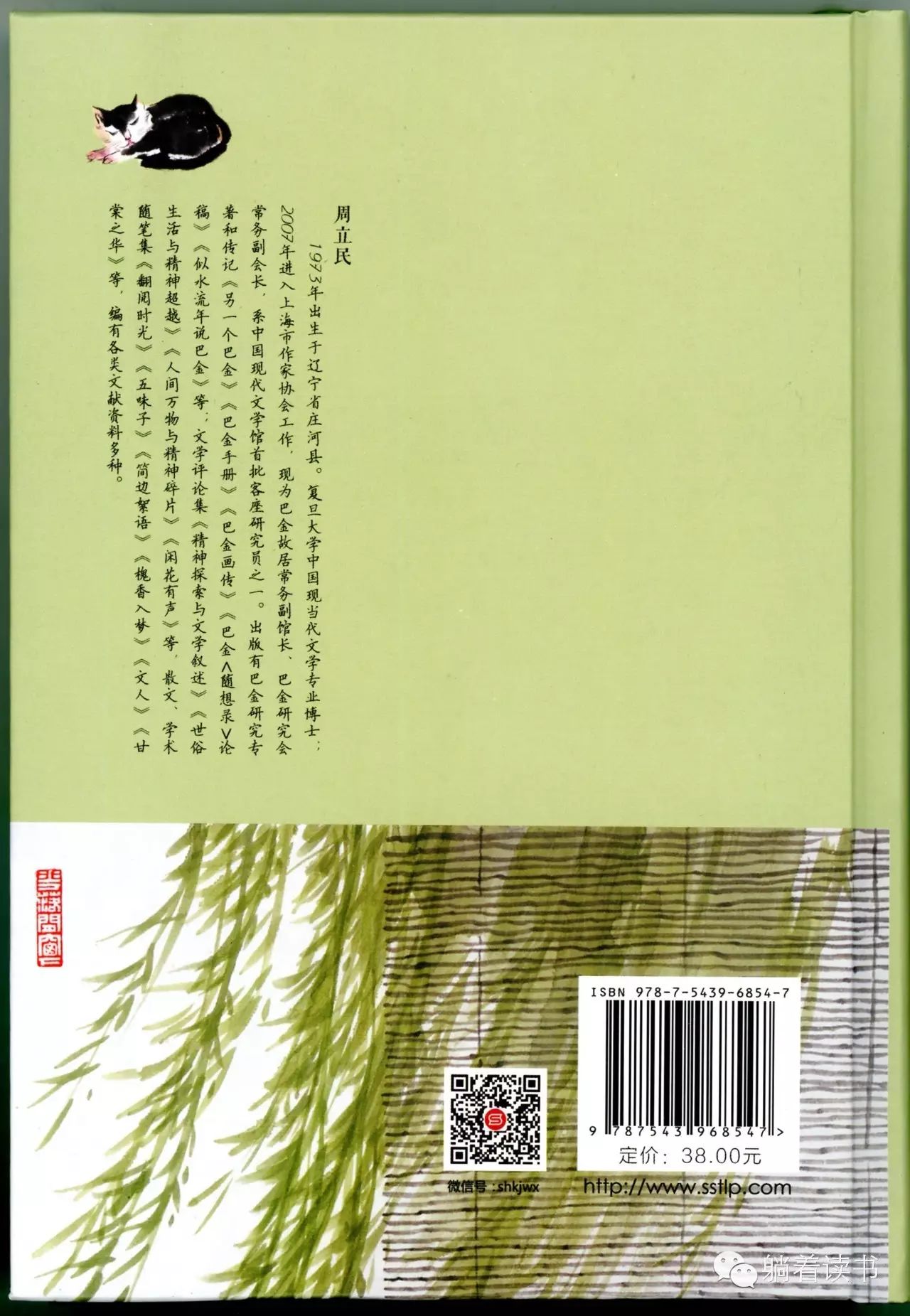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fwsgw.com/a/xinling/1996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