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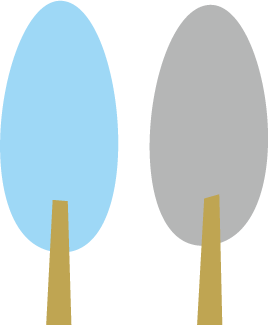
于丹为何这么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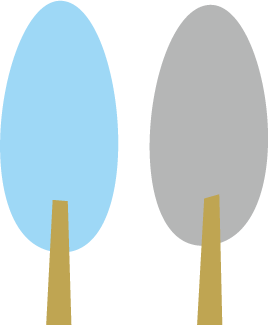
学术写作基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确实如施特劳斯所理解的那样,始终是对当下日常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介入。然而,学术写作中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专业术语写作,却大大降低了这种批判性。即便我们不走施特劳斯式的“写作”道路,即刻意而谨慎地使用微妙的专业术语写作,学术写作也难以完全避开各种晦涩难懂、令人生厌的“专业术语”。那么,“象牙塔”中的学术写作,一种永远无法完全“去专业化”的写作,如何才能使自己有力地批判性地介入日常的意识形态机器?换言之,这些包含(如果不是充满)专业术语的学术话语,如何与当下日常现实的“在世存在”发生关联?

齐泽克近二十年的思想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镜子。齐泽克是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思想斗士,他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20世纪思想家中最被公认为“行话之王”的拉康。但正如齐泽克本人在电影《齐泽克!》中所说,如今最喜欢他作品的读者不在学术圈内,而是在学术圈外。他的学术著作中蕴含着大量“另类”分析,分析对象从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到社会时事、八卦丑闻、网络虚拟生活、电脑游戏、饭桌上的政治玩笑甚至黄笑话,甚至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性与爱……他的学术写作与日常现实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往往一读便爱不释手。 于是,这个来自东欧小国、在英语学术界耕耘了20年(1989年至今)的思想家,如今在世界各地都有了粉丝。据说,许多好莱坞影视明星的床头卫生间里都放满了他的学术著作;而在上海“新世界”高档白领酒吧区,穿着廉价T恤的老齐一出现,就被眼尖的年轻女大学生拥上前来,要求合影……拉康的讲座和著作中那些晦涩难懂、深不可测的专业术语,在老齐的笔下化作万把刀,锋利而尖锐地刺入读者的当下存在。我在墨尔本的好友兼室友,一位本地读生物医学的博士生,经常在晚饭后听我聊齐泽克,有一天,他忍不住向我借了一本齐泽克的书,通宵读完。
这位过着风流生活的小帅哥第二天见到我时,不禁苦叹一声: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如此焦虑——我难道不是齐泽克所分析的“变态”吗?虽然拉康是齐泽克思想的核心来源,但齐泽克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很讨厌拉康身上那种法国思想家的矫揉造作和装腔作势。在一次下午茶闲谈中,齐泽克曾告诉我,他之所以在80年代中期成为拉康理论的坚定追随者和阐释者,并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被这个理论在“理性”上“折服”(当代有理有据的“理论”太多了),而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主义经验,对后期拉康的各种概念产生了一定的诱导和浸润;也就是形成了某种存在主义的“关系”。 如果一个概念不能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最终“关联”,他就会从内心深处对这个概念感到焦虑。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最近写的小册子《(如何阅读)拉康》并不是像该系列的其他书一样对拉康思想体系进行“严肃”或“纯学术”的介绍。读者真正读到的是拉康的深刻概念如何进入思想实践者(齐泽克本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它们如何与当前的意识形态产生批判性的“关系”。

因此,当代中国学术写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为什么读者要读你那些以专业术语为基础的写作,比如那些学术上“正确”的《论语》解读?几年前,我在给一位年轻朋友的一封信《论翻译与阅读》中,就中国经典名录提出问题:“读者首先要问自己,今天为什么要读《论语》(以及相关注释经典的整个体系)?这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当下的生存处境没有迫切的反思,那么阅读就不可能具有内在的探究视角,不可能具有生命存在性的迫切问题。”在那封信中,我强调了这一点:必须与自己所处的当下现实——甚至与自己(自己的“存在”)——建立“关系”,只有这样,全面的阅读努力才不是一种给别人看的“表面努力”,最隐秘的是给自己看。 “否则,即使花了‘几十年’,熟读了《论语》的字句义,不也只是一种表面的努力(“量”的努力)吗?换言之,如果没有遭遇到存在论的焦虑——这种焦虑永远是福柯所说的‘当下的本体论’(ontology of the present),那么,这个阅读计划就纯粹是一种个人兴趣的努力。 “今天人们为什么读《论语》?”销售量达千万册的《于丹》的“心得”与“感悟”给出了答案,为今天人们读《论语》找到了理由,尽管这个理由本身,借用“十博士”的话来说,完全是“庸俗”甚至是“媚俗”的。不过,尽管于丹对儒家思想的解读粗糙,在理论上充满谬误,但她的写作实践表明,她对儒家思想“道不远人”这一核心思想的理解,要比很多专业学者“身临其境”得多。在《于丹的《论语》思想》后记中,于丹如此谈及“道不远人”:
以我的学历和阅历,我绝对不敢去解释和分析《论语》。这就好比让我分析一下这温泉的化学成分,我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有精准数据的检测报告。我唯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用我的身体和血液去体会,就像两千多年来泡在这温泉里的几千万人一样,用我身体最敏感的病变部位去承受温泉带来的益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经典的价值,或许不在于让人敬畏,而在于包容、流动,能够温暖跨越古今,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延续着同一个目标、不同感悟的价值。所谓的真理,离人并不远,或许吧。在我眼里,真正的圣人,从来不会用晦涩难懂的典故吓唬人,也不会堆砌晦涩难懂的文字来烦人。
显然,于丹很清楚当代学术“大师”们的写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她干脆不在学术层面与那些批评者对峙,而是直指生活的实践与体验。她直言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晦涩难懂”、“难懂”的行话写作“吓唬人”、“困扰人”,根本就缺乏生活的“浸润”。一言以蔽之,当代学术话语根本就缺乏“用身体和鲜血去检验”的写作实践。于丹自己所写的“道不远人”是直指“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她把《论语》这样的古典文本与当下现实中的个体生命做了一种特殊的“联系”。而正是这种特殊的“联系”,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才真正需要最批判的关注。 它的逻辑是:人们只要能领悟《论语》和《庄子》(一碗中国古典版的“心灵鸡汤”)里的道理,就能真正每天过上“美好的生活”。

因此,透过“于丹现象”,我们真正看到的是,虽然于丹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借用她最激烈的批评者“十博士”的话来说——是对国学极为恶心的“剧透”“淫秽”和“性幻想”,但她那些“极其受欢迎”的公开写作(有人将各种相关媒体和争论汇编成一本畅销书《于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48)却确实触及了生活在当前意识形态秩序中的人的某种生存焦虑和生命焦虑——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如此渴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却又如此无助地寻找一种可以相信自己目前的生活是“幸福”的“依据”。
“于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如此深沉的焦虑!这就是“于丹现象”所清晰揭示的存在处境。在过去的2008年,于丹在说完“让逝者过上好日子”这句话之前,许多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刚刚睁开一双双黑亮的眼睛的新生命,就告别了毒奶中无“福”可享的“好日子”。“破碎的心,要到谁的院子里去?不等陨石落到西南去。”49于丹,“用身体和血液去检验”,摸摸自己的良心说,这是不是“好日子”!“淡定”,“平和”,“调整心态”,“安于贫贱,享福道”,“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去对着那些无助地哭泣的父母说一声! “这次地震是5月12日,母亲节就早一天,5月11日,我们想想,我们这一生,还能和父母一起过多少个节日?”官商勾结奶制品毒婴事件曝光后,于丹为什么不继续站出来喊话“保护孩子!以命偿命!”于丹端到人们嘴里的那碗“心灵鸡汤”,如果对其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检测报告”上不会出现“三聚氰胺”成分——它不像被列为“国家免检产品”的三鹿奶粉,通过可以“精准”检测出的“化学成分”毒害生命; 而是进入日常的意识形态,并“无形地”毒害——麻痹——整个心灵(心要“淡定”、“平和”,心态要“调适”、“安于清贫”、“学会克制”、“该放手时就放手”……)。马克思,以及一个世纪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阿隆都强调,无形的符号话语可以成为最毒的“鸦片”。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实践,就是在进行一场永无休止的“反鸦片”战争(永远不可能彻底取得完全胜利)。正如,尽管目前已经展开了一轮反毒奶粉斗争,但各种人们尚未意识到的准毒奶粉产品仍在市场社会中流通,无论进行多少轮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日常现实的每一个角落仍然会弥漫着意识形态的迷雾,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清除意识形态的“毒”。 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根植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的不可能性。
公共写作始终是对当前意识形态的介入,在意识形态中产生不同的“化学效应”(话语效应)。因此,它始终具有伦理政治的维度,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完全“去伦理化”和“去政治化”的话语。2008年之后,每一位中国意识形态实践者都应该重新听听马克思的墓志铭:仅靠各种学术话语来解释世界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
结论
因为公开写作永远与当下现实“相关”,永远是对意识形态秩序的“介入”,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介入是“驯服的”(如声称“以身试血”的于丹,以及表面上与她完全对立的专业学术精英们),还是批判的。《爱与死的幽灵学》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讨论激进的意识形态实践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在今天是否仍然可能。也许我的理论阐述(本书在理论上继承了齐泽克开创的很多哲学-精神分析方向)不能得到每一位读者的认同和认可,但这种写作行动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是对我所处当下现实秩序的批判实践。读者从中体验到的是一种呼吸和思考的日常生活,从中读到的是关于爱与死的个体生命实践。
虽然庄子曾说“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荀子也说庄子“蒙天而不知人”,但选择“有言”的庄子,也有一段类似于自我反省的话语:“知而不言,天之道也;知而言,人之道也。”作为“玄学”的鬼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字(话语);而它所讲的“知”,也不过是纯粹属于个体生命的知识而已。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fwsgw.com/a/xinling/2008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