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在川任教期间,讲课讲得一手好菜,声誉很好。当时华西大学的学生回忆说:“周先生上课讲北京话,起伏不定,很好听。周先生曾说,汉语是一座宝库,源源不断,宝藏迷人。”“周先生用英文讲课,英语流利好听,我们都听得入迷了……”1954年北调前,四川大学发出的正式鉴定函中,特别强调周汝昌先生是教学最出色,因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周先生晚年讲课时的风采和风度,通过电视传下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教程》就是根据周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课录音和录像改编而成的课件教材。讲课时的声音、手势、体态、神情,虽然在文字上难以呈现出来,但那种即兴的闲聊风格、悠然的语气,甚至言语中的韵味,却依然在。该录音录像节目由周先生的女儿伦玲女士全程录制,并由出版编辑精心编辑,加上后来撰写的前言、课后笔记、课后评语的提示、拓展、总结,已然转化为一部具有独立价值的专业著作,实属可喜可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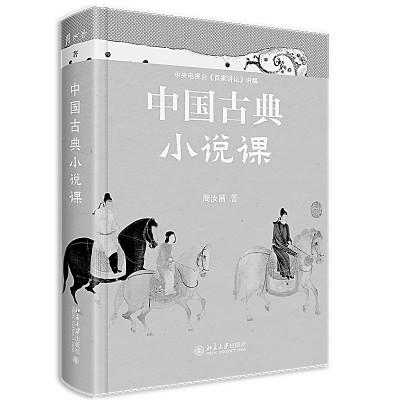
周汝昌著《中国古典小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
信任是基础,“文字”兼具信任与美好
周先生此次央视讲座以中国古典小说“四大经典”为主题,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编辑后的文本共有六讲,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只占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周先生的主要作品、他研究的对象《红楼梦》则占了三分之二。但并不给人一种参差不齐的感觉。周先生在开篇“引言”中表示,讲座的重点不在于“传递知识”或一般常识,只想“调动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大家一起思考、思考问题,引发听众从未想过的新意义和新体验。” 阅读课件文本后所获得的经验、启发和感受确实已经超出了话题的限制。
周先生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考据学家,但他非常重视概念的梳理。史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小说不同于追求哲学真理的西方小说。在第一次讲座中,周先生就提出了文学性与文学性的区别,真实与美的区别作为理论基础。周先生反复强调,历史作为野史、野史、杂史的小说,是以真实为前提的,只有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周先生认为,用小说这种通俗的形式去叙述国家的兴亡、世间的恩怨、天道的玄机,也是“四大名著”被称为“奇葩”的原因。从渊源上看,即便在中国小说传统中,《红楼梦》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史上最精彩的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文本”,也是因为真与美的结合。

清 沈潜 《红楼赋画册·海棠社赋》
方法、观点和精神背景
周先生讲课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方法论。关于《四大名著》,周先生讲的是创作方法、研究方法,还有阅读欣赏的角度和方式。在众多方法中,周先生最重视的是创作过程的联系、阅读的比较、研究的综合。周先生当然明白《四大名著》不在一个层次上,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断强调四者之间的联系。在讲授《红楼梦》的过程中,周先生经常指出这本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小说的联系和相似之处。周先生认为《西游记》中“石猴”的故事和《红楼梦》中“石头哥”的故事是有关联的。 天地人“三才子”背景下的历史、社会、文化联系,也是连接“四大经典”的纽带。在与其他三部小说的比较中,周先生尤其看重《红楼梦》“波浪式”推进的结构特点,重视前三部小说正面描写与《红楼梦》特殊写作风格的区别。王先生指出,三部小说可以直接阅读,解读以“一手两碑”风格写成的《红楼梦》,关键在于文本背后的考证与阐释。《红楼梦》前八十回与伪续集后四十回的对比,是王先生阐释的重点。《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对比、中西“悲剧”的对比,也是王先生关注的重点。 将传统的考据、义理、修辞融为一体,对文本进行综合的考证、分析和阐释,将历史研究、精神领悟和艺术欣赏融为一体,是王先生的治学之道,也是他的教学之道。
除了概念梳理和方法建议,周先生对一些关键问题也有自己的解释。《水浒传》是一部爱国遗民的作品,成书于宋代,不晚于元代,是周先生基于文本语言和内容所作的研究。不同于其他三部小说是在宋元以来的民间积累基础上形成的,《红楼梦》是个人自觉创作的结果。曹雪芹、他的书、他的人,自然成了周先生讲课的重点。周先生讲到《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尤其注重内外证相结合。书评人脂砚斋在讲解作者曹雪芹的家庭背景、成书过程、文本内涵的同时,也谈到了重点。 周汝昌先生在1949年12月发表的《脂砚斋评真石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脂砚斋的文本角色是史湘云的观点。周先生认为,作为曹雪芹的搭档,脂砚斋与金圣叹不同;脂的评语不是一般的小说评点,而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秦、脂两个人物是天作之合,但脂砚就是湘云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在于失传的《旧本》,不作进一步考证,很难验证。这一点,王先生的讲稿中也没有忽略。
分析“四大名著”读者群的不同社会属性,是周先生既有的小说研究思路。《红楼梦》作为一部囊括人生、家庭、社会、制度、伦理、道德、信仰等各方面的巨著,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相较于一般常识性的内容,周先生更看重“四大名著”的精神价值。用小说这种“通俗”的形式去为世间芸芸众生“阐释”,是周先生对《红楼梦》的基本理解,这种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对“四大名著”的评述。周先生认为,《三国演义》的“义”,《水浒传》的“忠”,《西游记》的“真”,都可以归结为《红楼梦》的“情”。 这一结论,也是理解《四大经》的精神实质。周先生以《大唐三藏圣教序》“断伪续真,开后世”来佐证《西游记》的“真”,再与《红楼梦》的“去伪存真”相联系,同样令人惊叹。在周先生看来,《三国演义》中的“英雄”、《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位绿林英雄、《红楼梦》的“情书榜”中的金钗,都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而“才子”的“命”的结论,也是周先生对《四大经》精神主脉的把握的结果。

佚名清《全图西游记》
地方话语体系重构模型
周汝昌先生对古代文学、古典小说和《红楼梦》的研究已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但他另有追求。1995年夏,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让“学”回归“红学”——百年来红学史的回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篇曾饱受批评的文章,其实是一篇基于学术反思的重建红学学科宣言。诞生于本土的“红学”与西方文论指导下的“红楼梦研究”的区别,是周先生在新时期之初就指出的。在《中国古典小说》的阐释中,周先生再次提出了古典小说研究中“红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题。 课件最后,周老师在总结“文化小说”的基础上,将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历史时期与甲骨文、敦煌学、红楼梦“三大学科”联系起来,背后的深意更是耐人寻味。
近代以来,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学术体系迅速崩塌。包括《红学》研究在内,人文学术研究,从概念、范畴、思想、方法、问题意识、具体模式到论证方法,几乎完全是模仿西方的结果。以《四书》为基本框架的传统中国学术,在吸收外来优秀学术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转型,是一个时代重大课题。这一重大课题在“五四”时期反对学衡派思潮的斗争中被提出,在陈寅恪先生构建“新宋学”体系的设想中,已经呈现出大致的格局。其实,本土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之所以成为近年来的热点,也是有历史原因和内在逻辑的。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科虽然也有一般的共性,但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民族性最为明显。 学术体系乃至学科体系的建设,都建立在本土话语体系的建设之上,相较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话语体系的建设尤为关键。
一般认为,话语体系是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的系统,其中概念、范畴、表达、理论、逻辑等要素是最基本的。其实,周老师从一开始就清楚即兴演讲与事先写好的演讲的区别,看似随口的演讲,不仅思路清晰,而且对语境预设、词语选择、演讲风格等都有清晰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话语体系的构建对于周老师来说确实是有意识的行为。
汉语的“雅语”在《诗经》时代就已成型,经过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的冲击和欧化思潮的洗礼,本应形成一套通俗化、科学化的新型汉语语言体系。然而,在经历种种干扰后,汉语的庸俗化、僵化趋势愈发明显。从学者的辈分来看,周汝昌先生无疑是一位成长于古今中西交汇时代的学者。周先生的一生坎坷,但早年形成的语言表达习惯却始终未变。集诗人之才、史家之学、儒家之心于一身的周汝昌先生不仅建构了自己的传统小说研究和以“曹学、版本学、志学、探失学”为主体的红学学科体系,而且在学术语言运用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作为一位老学者,周先生讲课时,用的是雅俗共赏的白话文和通俗雅语。古代任何时代使用的语言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代语言,而周先生口中的纯正汉语,更是可以翻译成英文的学术界通用语言。如此生动独特的课堂语言,对于李先生来说,是学术阐释、文化交流和心灵启迪的媒介。由讲义整理而成的《中国古典小说》文本,是隐含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构想的本土话语体系重建的典范。
本文图片均选自《中国古典小说教程》
光明日报(2022年8月29日第15版)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fwsgw.com/a/sanguo/2001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