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对“文化输出”这一说法是比较反感的,这是一个政治性很强、含义不清的概念。
比如,两年前上映的《真三国无双》电影版,就被调侃为“一部中国人根据日本人写的小说改编的游戏改编的电影,而小说是中国人写的,历史是中国人写的”。这是中国人输出日本,还是日本人输出中国?如果我们把这中间的步骤分解开来,一一定性,即中国人写《三国演义》传到日本是文化输出,中国人玩日本人做的《真三国无双》游戏是反向输出,中国人拍《真三国无双》电影版是强化日本的出口行为,那么你会发现,按照这个定义,日本的ACG作品大多是“输出”而不是“输出”。

目前日本ACG中最火爆的题材无疑是异世界冒险。这类背景模板大多设定在欧洲中世纪,除了主角是穿越者之外,其他角色一般都是欧洲人,建筑、风景、社会制度等也都来自欧洲。这种背景模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人开发的桌游《龙与地下城》。
在日本的ACG作品中,随处可见外来文化的踪迹,混杂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人做的真三国无双,甚至很多看似属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东西,其实都受到了西方的强烈影响。比如忍者,就是文艺作品中的常客,它们在近代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美人,尤其是美国人对其很感兴趣。20世纪70年代,一些忍者题材的cult电影就被拍了出来。日本的创作者们并没有强烈批判美国人对日本文化的扭曲和亵渎,而是积极迎合这些被西方人转化的印象,创作出了《忍者龙剑传》《忍者蝙蝠侠》等符合美国忍者形象的作品。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动画创作像日本动画一样,充斥着尼伯龙根、诸神黄昏、源平战争、维京海盗、西部牛仔、中世纪城堡等元素,用欧美风格制作中国故事,那么人们绝对不会反应出中国的文化输出做强了,而是被外国人输出成了筛子。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文化输出”是一个定义标准极其不明确的概念。同样的事情,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榜样,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失主权、失国耻。
我写这些,并不是想批评文化输出的观念模糊,观众的包容度不够,而是想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日本和中国虽然渊源深厚,但国情还是有很大差别。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学日本,可以想象,国产动画会成为一个被诟病已久、随时等待被点燃的火药桶。
我把中国人这种特殊的文化观念叫做“文化民族中心主义”。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本土文明,虽然受到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从古至今,中国基本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在中华文化圈,中国具有绝对的正统地位。另外,由于从古至今地理上的孤立,中国不愿意融入任何外来体系,而是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模式。
这种局面在近代中国积弱积贫时几乎被打破,并像其他文明一样被整合重组。但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之后,无论是朝野,都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而是试图重建原有的独立体制。这是好事,也是最适合中国政治文明的形式,但问题在于,这不是文化行为,文化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政治文化体系重构中,“文化输出”与“意识形态输出”一样,是一种政治行为,其内容十分复杂,很难概括为“拍出好的作品给外国人看”。比如,中国人拍中国电影,外国人拍得叫好,主角形象拍得非常好,就被认为是成功的输出;中国人拍中国电影,外国人拍得叫好,主角形象拍得非常差,就被认为是讨好外国人,是输出的失败,甚至是被外国人输出。更奇怪的是,如果美国电影里中国人打武术,日本人开高达,就算是美国电影,也算中国人输出或日本人输出。
这个复杂而又奇怪的原则,衍生出了一个支撑术语,叫“文化霸权”。文化霸权这个词,其实准确地概括了文化输出的最终目的,就是掌控文化产品的内容定义权。中国人应该长什么样,美国人应该长什么样,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社会地位、精神状态,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掌控。从这个角度看,“文化输出”就是要实现一个完全的政治目的。
利用文化实现政治目标是十分常见的手段,尤其是对于那些急于提升自身形象和政治话语权的国家来说。其中最为极端的便是韩国。韩国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随后用各种手段提升韩国文化的影响力。然而与具有文化民族中心主义的中国相比,韩国由于自身文化地位的弱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一切事物都捆绑在自己身上,甚至将炸鸡、啤酒等作为韩国的文化符号进行推广。

中国这件事情的特殊性,就在于行政与文化的捆绑关系。有人曾提到,“老干部作风”是“文人文学”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它与文人群体有着很深的联系,而且在两者逐渐解绑之后,仍然受到各种行政干预。
中国文学起源于垄断知识的统治阶级,早期作家均有官方背景,甚至作品也大都来自官方文件。加之无与伦比的行政管控能力,就连民歌也由专门的机构收集,需要经过官方文化名人认证后才能流传。这使得我国的文艺创作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家国情怀和对世人的警示。备受推崇的文艺作品甚至学生习作都属于这一类。
即便在印刷术诞生之后,民间知识分子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也无法撼动它,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高强度的管控至今未停,就连演员在90年代改革前都有国营职位,作协仍在积极招募网络作家。文艺从业者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市场,这种绑定关系让政府和民众都能毫无障碍地接受文化输出的概念,却忽略了现代文艺创作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
其实,业内人士早已得出结论,由于本土市场的复杂性,以及早年广播公司对播放权的垄断,日本动画并未能成功拓展海外市场。日本动画真正在全球走红是在2010年代,也就是视频播放平台和网络播放版权建立之后。讽刺的是,全球大型版权视频播放平台无一不是日本人建立的。换言之,日本人为自己制作的日本动画,被一群外国人传播到世界各地,日本人自己并没有为日本动画所谓的“输出”付出努力。
这其实就是商业社会的特性,消费行为自发地填补了两个环节之间的空白,与行政干预完全相反。你会发现,当科层制的行政管理模式运用到文艺创作中时,由于其反商业性,往往会起到反效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时,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取悦观众、创造收益,其他价值都是附带的。即便是个人风格很强的作品,也是为了寻求共鸣,但反商业的产品不是这样。
10多年前,日本上映了一部名为《未闻花名》的动画,讲述的是一群六人因为女主角意外死亡而分崩离析的故事。十年后,女主角突然以鬼魂身份回归,并帮助其他五人和好。这部以友情为主题的动画意外地带动了故事发生地埼玉县秩父市的人气,导致当地游客数量激增,随处可见《未闻花名》的广告牌,神社也出售以动画为主题的绘马。
《未闻花名》本身并无任何当地风土人情宣传元素,影片中甚至没有出现任何地名。故事发生地对剧情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因为编剧冈田真理的个人要求,才在家乡秩父市拍摄。《未闻花名》真的能算得上是一部“旅游宣传片”吗?如果要求动漫产业输出文化,其实就和用看旅游宣传片的眼光来看《未闻花名》差不多。

未闻花名
同时,日本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因为它拥有当今世界上几乎最少禁忌的创作环境。由于日本在战前和战时实行了完全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文艺创作政策,美国在战后执政期间制定了政府不得干涉文艺创作的法律。事实上,日本动漫和游戏创作者最害怕的并不是政府,而是民间的审查组织和社会活动家。
漫画之神手冢治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创作漫画《我的孙悟空》时,曾因戏仿、篡改名作、腐蚀儿童而遭到家长和社会的猛烈批评。上世纪六十年代,周刊漫画《少年Jump》以暴力、色情为卖点,吸引学生读者,几乎每期都有露出女性内衣的情节,被家长视为毒瘤。如果说这些还不构成具体的社会风险,那么,七十年代日本左翼赤军中不少人是连环画(漫画的一种)的爱好者,聚会时经常携带连环画单行本,并未中断日本漫画的发展。即便到今天,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地方议员积极推动立法限制甚至禁止ACG作品,可以说日本ACG靠着与这些民间人士的斗智斗勇才存活了几十年。
且不说行政手段最为强势的政府,中国观众与非观众与其他国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事实上,由于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观众至今尚未完全接受将文艺作品视为“娱乐产品”的观点,而是要求作品和创作者在商业活动之外承担起社会文化义务,会不由自主地将作品抬高。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如分析少年漫画中的政治博弈、从超级赛亚人变身探索脱亚入欧心态等现象,以至于当人们不喜欢某部作品时,通常不会说作品不好,而是会上升到政治层面,怀疑作者的政治立场,最起码也会被扣上“三不正”的帽子。
因此,如果艺术与行政分离,全面商业化,观众的反应恐怕不会比政府弱。同时,商业化也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至少在“资本”二字在大众文化中被赋予了太多额外含义的2022年,大多数人大概都已经意识到了商业化的负面效应。事实上,韩国在放松文化管制之后,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作品并非挑战禁忌的作品,而是形形色色的色情片,色情片依然占据着韩国每年电影产量的最大比重。香港电影业最辉煌的时候,数量最多的不是影迷们熟悉的枪战片或动作片,而是低成本的七天鲜片和名字早已被遗忘的三级片。
优秀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主流,而是从大量的垃圾中筛选出来的。但以我们对文艺作品乃至演员、导演本身的高标准,我强烈怀疑我们能否容忍这样以主流为下限的局面。不难想象,如果放宽规定,最受资本兴奋和青睐的,很可能不是受挫多年的个别导演,而是抖音短视频、网络电影,甚至是头条营销号的导演们。
说了这么多,是想指出,单纯拿中国动画和日本动画做比较并不合适,日本的创作模式也很难照搬。如果要求动画这种面向青少年的文化产品“输出”,那就太重了,超出了它应该承担的范围。但话说回来,我们习惯让文艺创作承担太多的重量。如何实现平衡?恐怕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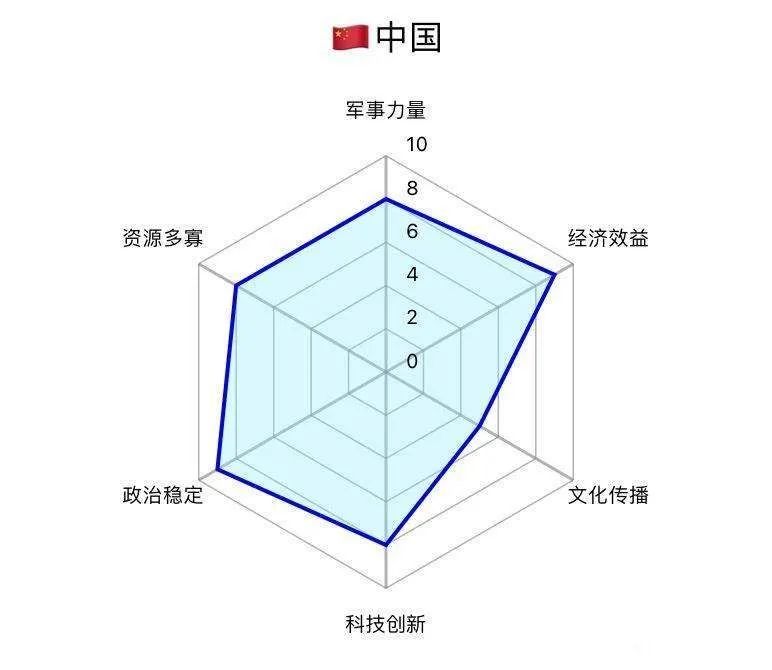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fwsgw.com/a/sanguo/201511.html
